作者:穆玉苹
随着制造业基础回流乏力而国际竞争局势愈趋紧张,近年来美国官方和智库愈加重视国防工业在面临紧急情况下的响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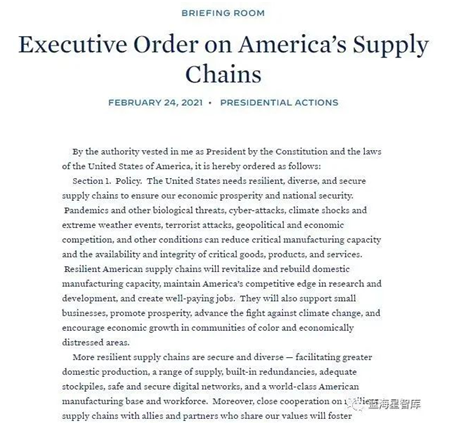
图1美总统拜登2月24日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旨在强化美国国防工业等制造业在面临国家安全和发展紧急威胁时的弹性与韧性
一、概念认识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在年度报告《美国军力指数2021》中,专门分析了大国竞争下国防工业的弹性和韧性问题,并提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构成:包括远超10万家的“以国防部等政府部门为客户、参与国防能力建设”的各类规模的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还有规模较小的“建制内工业基础”,以及不断扩大的“商业部门创新伙伴”。为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国防工业基础的应急应战动员水平由三方面要素来决定:
能力:国防工业基础的当前能力是否满足需求?正在发展的装备和技术是否为响应当前、未来国家安全挑战所必需?
潜力:国防工业基础保持多少冗余可谓恰当?正在建设的制造业基础能否满足持久冲突下激增的需求?
弹性/韧性:如何全面动员国防工业的“能力”和“潜力”,支撑未来应急应战?例如,在重大危机时能以多快速度扩大或调整生产线,来满足国防工业新需求?
三者中,维持国防工业基础“能力”与“潜力”的平衡是关键,“弹性/韧性”则是平衡的结果,但决定了国防工业基础最终的应急应战水平。因此,需要就这三个方面,协调好政策关注度和资源倾斜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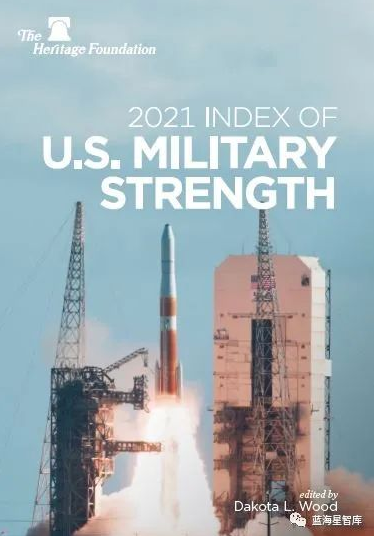
图2《美国军力指数2021》封面
二、历史经验
在历次战争和紧急情况下,美国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以有效调配资源,响应紧急需求。
1、一战期间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然已是工业强国,但发展重点在商业领域,国防工业仅有数量有限的兵工厂和造船厂,未做战争准备。参战后,美国实施大规模政府干预和行政强制手段,如提供“超额利润税”以激励企业的参与、接管私营企业以直接指导生产和解决劳资纠纷,并支持企业高管组建了战争工业委员会,由高层亲自监督战时生产工作。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生产了200万支步枪、8万辆卡车和1.2万架飞机。不过,这些装备因制造出的时间太晚,绝大多数并未运抵前线发挥作用。
2、二战期间
20世纪30年代欧洲战争开始后,尚处中立的美国即看到了国际军品需求带来的盈利机遇,提出建设“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构想,开始加强工业动员。其大幅提高军费,如将1940年陆军军费从2400万美元增加至7亿美元,并创建了众多政府组织,如战时生产委员会、复兴金融公司等,指导和监督将公共资本大量投入于新船厂、工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效显著。这些设施交由私营企业管理,也就此开启了国有民营的新模式。二战中,全国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被调动起来,扩大或改造其生产线以从事武器装备生产。到1943年,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力已达德国和日本之和的两倍。
3、朝鲜战争和冷战期间
二战结束后,美国从处理国有民营设施开始,将私有化扩到了整个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有效动员工业力量应对国防经济需求,美国颁布了《国防生产法》,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调整生产优先顺序、调配特定资源、资助国防工业基础能力建设等特殊权力。总统下还设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也执行相关权力。期间,政府曾试图延续历史做法,以行政手段强制没收私营企业,但因工人罢工而中止,并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
冷战期间,国防预算始终维持在超过GDP5%的高位,但美国寄厚望于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国防工业实施规划和投入。数十家私营企业承包了当时舰船、飞机、车辆等主要装备的业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工业综合体”。
4、反恐战争
21世纪初,“911”事件的发生使国防工业基础主要致力于发展反恐能力,其实力“完全可以胜任”,如开发生产了更先进的防弹衣和车辆装甲。期间工业应急应战能力的建设主要与资源调配有关。如紧急应对简易爆炸装置(IED)带来的主要威胁,期间政府调整了采办任务优先顺序,使防地雷反伏击车等装备得以紧急生产交付。同时政府还通过放宽对外采购,以解决国内在防弹玻璃、钢板等材料、部件方面产能短缺的问题。
5、疫情期间
由于美国个人防护装备和许多药品的生产基本已转移海外,新冠疫情成为检验美国工业基础应急能力的“试验场”。总统启用《国防生产法》分配权,优先安排满足国防和紧急战备计划要求的合同和订单,特别是卫生和医疗资源。政府机构援引《联邦采办条例》的紧急条款加快合同审批,并加大对快速采办合同的使用,在3D打印、生物制造、纺织品等领域,吸引更广泛的企业参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进一步推动国内相关供应链的加快建设,这其中包括向《国防生产法》基金注入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拨款(10亿美元),并取消部分限制条件,使资金能尽快投入使用。

图3美国工人在生产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口罩
三、当前问题和举措思路
当前,美国正一方面通过投资短板能力、加强外资审查和安全保密管理等方式,健全国防工业的供应链,提升紧急事态下的韧性,另一方面通过吸引非传统供应商、扩大国际合作等,来扩大国防工业的基础,增加冗余供给能力。但传统基金会认为,随着国家防务重点转向应对新一轮大国竞争,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应急应战能力方面仍存在隐忧。
首先,近20年一直将重点投向反恐战争,一旦发生危机,国防工业基础是否有能力迅速扩大复杂大型装备(卫星、飞机和船舶等)的生产能力。其次,高新技术的扩散和经济全球化,催动美国制造业向“临时制造”和“全球供应链布局”转型,很多关键子部件、材料的生产业务转移到了海外,特别是竞争对手国。此外,国防工业供应链安全性存在挑战,一方面源于供应链的网络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防部对底层供应链情况缺乏足够掌握,易出现供应失控。
为此,美国传统基金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统筹提升“能力”“实力”“弹性”三方面水平的角度,提出了政策措施建议:
加强“能力”方面:扩大国防工业基础,吸引更多非传统供应商的加入;利用国防工业能力投资和其他权限、项目,消除对竞争对手国的依赖;加强灵活、快速采办机制的经验总结和推广,为危机时加快开发、生产和交付能力做好准备。
提升“潜力”方面:扩大签署《国防生产法》第七章中,关于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危机时协助保障国防”的自愿协议;增加原型采办,并促进原型采办与生产项目的联系;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调查,增加对国防供应链情况的掌握;借势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的颁布,储备更多与大国竞争相关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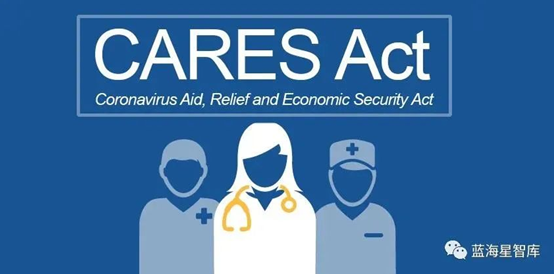
图4《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宣传图
实现“弹性/韧性”方面,协调《国防生产法》等权限、政策、责任,提前做好应急应战的计划和组织安排;提前做好应对网络攻击、卫星攻击、疫情等紧急情况的准备,如对国防供应商推行强制性的“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